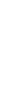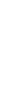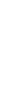| 上一章 | 目录 | 下一章 |
第731章 踢斛淋尖
罗家堡大桥前,
牛车排起了长队,车上装著满满的粮食。
大桥过去,无极堡旁便是新设的御宿镇义仓粮库。原本义仓是要设在州县城中,御宿镇得皇帝特旨,在镇上设立了义仓。
昨日跟皇帝宰相们共饮酒,还得赐封民爵一级,一眾乡里豪强地主们,回去路上就已经商议好了,
今日便要把这义仓粮纳了。
各自回家,那是连夜就召集长工、佃户们,从仓里称量粮食,一早上就装车送来。
桥这头,
镇长郭二和镇副罗三,也是昨晚便知晓今早会有这齣,也是早早就做了准备。
罗二今天一身浆洗的笔挺的长衫,迎头向两位镇长走来。
“义仓建立,我罗老二来纳第一份粮,家里塬上塬下八百亩良田,御宿乡以外还有两千亩地,
按新规,哪里的地就在哪里纳粮,
我今个把八百亩的义仓粮送来了,亩纳两升粟,总共十六石粟。”
郭二郎笑著道:“还是老哥积极啊,你这是纳粟纳麦还是纳稻穀?”
“我家地塬上种麦塬下种稻,我纳麦子。”
郭二又问,“是今夏新麦还是粮仓里的旧麦啊?”
罗二瞪了他一眼,“郭乡长,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?当然是今夏才收的新麦子。”
“好好好,惯例,三斗麦折五斗粟,你这八百亩地,要纳十六石粟,你交麦子,就折九石六斗麦子。”
“杜仓督,带人量粮了。”
新任义仓仓督姓杜,是隔壁樊川京兆杜氏族人,御宿镇仓督和市令一样,都属於流外吏。
不过职权还是挺重的。
杜仓督跟郭二那也是亲戚,笑著叫上市吏,取来仓斗。
为示公正,还特意又取来了市集上的市斗,还有百姓家的民斗,一起先核对了一遍,这仓斗確实不是大小斗。
罗二家的长工,赶著两辆牛车过来,第一个纳粮。
现在还没正式清量过田亩这些,罗二他们属於自申自纳,到时清量田亩后再多退少补。
“量吧,今年新麦子,我这两车麦子,一车五石,在家量的可是堆尖的。”
长工把粮食搬下牛车,
杜仓督开始查验粮食,要查是否霉变陈旧,有无掺杂石子泥灰等等。
查验合格后,才开始斗量。
粮食要一斗斗的过数。
麦子倒入仓斗,装满后,仓吏惯例要去踢斗,杜仓督和这几位仓吏,都是从长安太仓调来的,那都是老仓吏。
仓吏踢斛那是吃饭的看家本领,验收称粮之际踢斗,能让斗里粮食更加紧密,装的更多。
而往外出粮的时候,他们可不会踢斗,一来一去,就能多出不少粮来,这就是他们的灰色收入了。
这踢斗也是门学问,有的人踢上几脚,也不能再腾出多少空来,可有的人看似不起眼的一脚,却能让装满的斗再腾出很多空。
杜仓督叫住了今日换上了內衬铁包头鞋的仓吏,
“司徒有令,义仓收受仓粮,听令纳户自行概平,不得踢斛淋尖。”
“敢有多收斛面者,杖一百!”
杜仓督这不轻不重两句话,让准备大展神威的仓吏愣住。
“仓督,踢斛淋尖,向来常规啊。”仓吏辩言。
“你要去跟司徒讲讲这个常规吗?”杜仓督瞪了他一眼。
也不看看这是哪,这是无极堡旁的御宿镇义仓,
今天第一个来纳义仓粮的是李司徒妾侍的父亲,昨晚皇帝还带著眾宰相在罗二家吃酒,还赐了他民爵一级。
你踢他的斛淋他的尖?
今天,
绝不能玩那套。
杜仓督拿来一块刮板,一斗装满后刮平斗口,“罗二叔,咱这每斗都是装满后刮平,绝不会踢斗淋尖,这刮下来的也还是你的粮。”
仓吏们站在一边,看著那刮下来的粮食,总觉得肉疼。
按老规矩,他们收粮,要先踢斗,把斗里的粮踢的密实了,然后还要再往上装,要堆起一个尖尖来,最后再踢一脚。
斛上粮食洒下来斗却不倒,这洒落的粮食就算损耗,归他们所有。
別看这踢斛淋尖,徵收一石至少要踢下来两三升。
每一斗,装满后刮平,刮下来的粮食却不属於他们,如何不让人心疼。
“十二石三斗夏麦。”
量完,杜仓督大声宣布。
罗二大声的道,“咱在家那都是量好的,我八百亩地该纳十六石粟,折麦九石六斗,算上两成的鼠雀耗,再加一石九升二,总共就是十一石五斗二,
再算上踢斗淋尖的,一石加三升,再加三斗,总共是十一石八斗。
我呢还多拉了五斗来,正好是十二石三斗。”
罗二捋著鬍鬚:“杜仓督这斗量的很准,丝毫不差。”
“把粮食帮忙搬进仓吧。”他对家里长工道。
杜仓督却笑著拦住他,
“不急,我来任这御宿镇仓督,虽只是不入流的杂任,但也有幸见到了李司徒和杜僕射,
李司徒说了,御宿镇义仓收粮,不许踢斛淋尖,更不许用大斗进小斗出,
这收粮时,雀鼠耗统一为每石加两升,不得多加。”
“罗二叔你家在本镇共有良田八百亩,那便须纳义仓粮十六石粟,加征三斗二的雀鼠耗,总计十六石三斗二升粟,折麦则是九石七斗九升二。
就按这个数字徵收、入仓,多的一分一厘都不能收啊。”
“你们几个,量出九石七斗九升二麦子,多余的帮罗二郎装好,一会再带回家去。”
罗二有点意外,“这粮都运来了,哪里还有再运回家去的道理,我这也都是按以往惯例,一石加二斗的耗羡,每石约三升的斛面···”
杜仓督上前,拉著罗二的手,“老哥唉,咱这可是陛下特赐钦设的御宿镇,这义仓也是头一个设在县以下的,
这可是皇帝和宰相们都盯著的,岂能乱来。”
將差不多九石八斗的麦送入义仓中,成为御宿镇义仓储备的第一批粮食。
登记签名按手印,给予一张纳义仓粮的凭证。
这一幕,
看的一眾人都很意外,
乡绅豪强们意外,
升斗小民们更意外。
啥时候,这征粮时不想著法多收,还会把送去的粮给推出来的。
有人似乎突然回过神来,激动的大声问,“杜仓督,这一石粮只加二升雀鼠耗吗?”
雀鼠耗,名义上是补偿仓储损耗,可实际上这也是地方官吏们的一个灰色收入,
甚至到底加征多少,也往往是各地说了算的,
隋乱年间,这雀鼠耗甚至一石加二三斗,甚至有加四斗的。
而如今,居然统一了这个雀鼠耗,一石只加二升,还规定了这个耗羡加征,得入公帐,成为地方官府的公费。
將取代公廨钱放贷收息,用於公廨支出。
原来一石加二三斗,甚至四斗,现在一石只加二升,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。
过去课户,一丁一年要纳地租两石,可纳粮要送到州县,结果两石粟,要加五六升的斛面,还得加上五六斗的耗羡,实际负担增加了三成左右。
罗二也是清楚这些,所以今天都是提前多准备了的。
结果,居然不踢斛淋尖,还只每石加二升的耗羡。
还剩下了两石五斗的麦子。
罗二觉得这是因自己女婿是司徒,昨天皇帝还在他家喝过酒的缘故,坚持要把这剩下的两石斗麦子也送进仓。
“罗二哥哎,真不能坏了规章制度。你这两石半麦子,可以捐入社仓嘛,
咱这不是还有社仓嘛,完全民间村社自己所设,自愿捐献,自己管理,救助本社村民优先。”
在杜仓督的一番劝说下,
罗二最后决定,把这剩下的两石斗麦子也不拉回家,捐进御宿社仓,这是乡民们自己管理,不强制缴纳。
“想不到啊,
这义仓粮亩纳二升粟,还真就是二升,百亩地两石粟,再加四升鼠耗而已,一点斛面都不收。”
眾人都是议论纷纷,这样的好事,还真没遇到过。
除了社里的义仓,会里的会仓收粮,不管那些,官仓纳粮哪见过这样的。
习惯了以往的那套,现在还突然有点不適应呢。
各家的牛车拉著粮过来,陆续完粮,
几乎家家都是按老规矩多准备了粮,然后都没有多收。
有罗二带了头,其余乡绅们倒也没谁好意思,把剩下的那几石几斗的粮再拉回去,也都捐入社仓。
郭二郎也趁机对围观的乡民们道:“诸位父老乡亲,朝廷新政,惠及百姓。
这义仓粮亩纳二升,一石只加二升的鼠耗,没有踢斛淋尖收斛面,这马上也秋收了,大家赶在入冬前,儘快把这义仓粮缴纳了。
就咱本乡缴纳,也无须送到长安,方便著咧。
接下来,镇里要开始组织大索貌阅,严查诈老诈小,隱匿人口,没有户籍的要抓紧来登记为客户,
客户无须纳租调,有了户籍以后,也是朝廷编户良民,再不用提心弔胆过日子了。”
“这个冬季还要清量田地,镇里所有田地都要重新丈量,然后確权换契,大家相互转告,如实申报,配合丈量,完成登记確权换契,谁要是隱匿田地,到时可是要没收充公的。”
···
普济院中,
大皂角树下,
十男十女,二十名院中孤儿站成两排,
院长牛义感看著这群孩童,也有几分不舍。
“这是代王府送来的新衣,你们都去换上吧,一会呢,你们就去无极堡,跟著去长安。
你们是幸运儿,能被天子和宰相们选中领养,不管是进了宫还是去了宰相家,一定要自强自尊自立。”
李恩义站在那里,听著院长的谆谆教诲,目光却不由的瞥向旁边的李恩泽。
李恩泽是二班的班长,跟他同龄,也是十岁了。
他將前往代王府,由代王领养。
李恩义很羡慕他,他被皇帝选中,要带到宫中同功臣子弟一起抚养。可內心里,李恩义其实更希望能够是代王领养他。
在他心中,代王是他的父亲。
如果能跟李恩泽换一下,他会毫不犹豫。
另一边,几百双同学们的目光望向这二十个幸运儿,充满羡慕。
被皇帝、宰相领养啊,这是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
无极堡。
李逸终究还是要返京了,
不止他捨不得离开,一群孩子们更捨不得离开。
“淑娘呢?”
小丫头一人躲在角落抹眼泪。
“怎么了,捨不得这里了,我们有空就可以回来,离京城也就三十里地而已。”李逸抱起丫头安慰道。
“阿耶,淑娘想求你个事。”
“跟阿耶还说什么求,啥事?”
“我听说那家人日子过的苦,有常年臥病吃药的老娘,那家女人也身体不好,孩子又生的多,年年欠饥荒,还住在破窑洞里,我想,我想把我攒的钱给他们买五十亩地,再买头牛,然后请人给他们修一修几孔破窑,好不好?”
李逸知晓丫头说的是她隔壁村的亲生父母。
“没想到你攒了这么多钱啊?”李逸笑道。
“我问过了,买五十亩地再买头黄牛,再修一修几孔旧窑洞,我攒的钱应当够。”
“你为什么想这样做?”
李淑低头,“毕竟我是她们生的。”
“没想到你从小就这么善良,行,我让罗三帮你把这事办了。”
“谢谢阿耶,淑娘永远是阿耶的女儿,我长大了一定会好好孝顺阿耶的。”
“那你亲我一下。”
(本章完)
罗家堡大桥前,
牛车排起了长队,车上装著满满的粮食。
大桥过去,无极堡旁便是新设的御宿镇义仓粮库。原本义仓是要设在州县城中,御宿镇得皇帝特旨,在镇上设立了义仓。
昨日跟皇帝宰相们共饮酒,还得赐封民爵一级,一眾乡里豪强地主们,回去路上就已经商议好了,
今日便要把这义仓粮纳了。
各自回家,那是连夜就召集长工、佃户们,从仓里称量粮食,一早上就装车送来。
桥这头,
镇长郭二和镇副罗三,也是昨晚便知晓今早会有这齣,也是早早就做了准备。
罗二今天一身浆洗的笔挺的长衫,迎头向两位镇长走来。
“义仓建立,我罗老二来纳第一份粮,家里塬上塬下八百亩良田,御宿乡以外还有两千亩地,
按新规,哪里的地就在哪里纳粮,
我今个把八百亩的义仓粮送来了,亩纳两升粟,总共十六石粟。”
郭二郎笑著道:“还是老哥积极啊,你这是纳粟纳麦还是纳稻穀?”
“我家地塬上种麦塬下种稻,我纳麦子。”
郭二又问,“是今夏新麦还是粮仓里的旧麦啊?”
罗二瞪了他一眼,“郭乡长,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?当然是今夏才收的新麦子。”
“好好好,惯例,三斗麦折五斗粟,你这八百亩地,要纳十六石粟,你交麦子,就折九石六斗麦子。”
“杜仓督,带人量粮了。”
新任义仓仓督姓杜,是隔壁樊川京兆杜氏族人,御宿镇仓督和市令一样,都属於流外吏。
不过职权还是挺重的。
杜仓督跟郭二那也是亲戚,笑著叫上市吏,取来仓斗。
为示公正,还特意又取来了市集上的市斗,还有百姓家的民斗,一起先核对了一遍,这仓斗確实不是大小斗。
罗二家的长工,赶著两辆牛车过来,第一个纳粮。
现在还没正式清量过田亩这些,罗二他们属於自申自纳,到时清量田亩后再多退少补。
“量吧,今年新麦子,我这两车麦子,一车五石,在家量的可是堆尖的。”
长工把粮食搬下牛车,
杜仓督开始查验粮食,要查是否霉变陈旧,有无掺杂石子泥灰等等。
查验合格后,才开始斗量。
粮食要一斗斗的过数。
麦子倒入仓斗,装满后,仓吏惯例要去踢斗,杜仓督和这几位仓吏,都是从长安太仓调来的,那都是老仓吏。
仓吏踢斛那是吃饭的看家本领,验收称粮之际踢斗,能让斗里粮食更加紧密,装的更多。
而往外出粮的时候,他们可不会踢斗,一来一去,就能多出不少粮来,这就是他们的灰色收入了。
这踢斗也是门学问,有的人踢上几脚,也不能再腾出多少空来,可有的人看似不起眼的一脚,却能让装满的斗再腾出很多空。
杜仓督叫住了今日换上了內衬铁包头鞋的仓吏,
“司徒有令,义仓收受仓粮,听令纳户自行概平,不得踢斛淋尖。”
“敢有多收斛面者,杖一百!”
杜仓督这不轻不重两句话,让准备大展神威的仓吏愣住。
“仓督,踢斛淋尖,向来常规啊。”仓吏辩言。
“你要去跟司徒讲讲这个常规吗?”杜仓督瞪了他一眼。
也不看看这是哪,这是无极堡旁的御宿镇义仓,
今天第一个来纳义仓粮的是李司徒妾侍的父亲,昨晚皇帝还带著眾宰相在罗二家吃酒,还赐了他民爵一级。
你踢他的斛淋他的尖?
今天,
绝不能玩那套。
杜仓督拿来一块刮板,一斗装满后刮平斗口,“罗二叔,咱这每斗都是装满后刮平,绝不会踢斗淋尖,这刮下来的也还是你的粮。”
仓吏们站在一边,看著那刮下来的粮食,总觉得肉疼。
按老规矩,他们收粮,要先踢斗,把斗里的粮踢的密实了,然后还要再往上装,要堆起一个尖尖来,最后再踢一脚。
斛上粮食洒下来斗却不倒,这洒落的粮食就算损耗,归他们所有。
別看这踢斛淋尖,徵收一石至少要踢下来两三升。
每一斗,装满后刮平,刮下来的粮食却不属於他们,如何不让人心疼。
“十二石三斗夏麦。”
量完,杜仓督大声宣布。
罗二大声的道,“咱在家那都是量好的,我八百亩地该纳十六石粟,折麦九石六斗,算上两成的鼠雀耗,再加一石九升二,总共就是十一石五斗二,
再算上踢斗淋尖的,一石加三升,再加三斗,总共是十一石八斗。
我呢还多拉了五斗来,正好是十二石三斗。”
罗二捋著鬍鬚:“杜仓督这斗量的很准,丝毫不差。”
“把粮食帮忙搬进仓吧。”他对家里长工道。
杜仓督却笑著拦住他,
“不急,我来任这御宿镇仓督,虽只是不入流的杂任,但也有幸见到了李司徒和杜僕射,
李司徒说了,御宿镇义仓收粮,不许踢斛淋尖,更不许用大斗进小斗出,
这收粮时,雀鼠耗统一为每石加两升,不得多加。”
“罗二叔你家在本镇共有良田八百亩,那便须纳义仓粮十六石粟,加征三斗二的雀鼠耗,总计十六石三斗二升粟,折麦则是九石七斗九升二。
就按这个数字徵收、入仓,多的一分一厘都不能收啊。”
“你们几个,量出九石七斗九升二麦子,多余的帮罗二郎装好,一会再带回家去。”
罗二有点意外,“这粮都运来了,哪里还有再运回家去的道理,我这也都是按以往惯例,一石加二斗的耗羡,每石约三升的斛面···”
杜仓督上前,拉著罗二的手,“老哥唉,咱这可是陛下特赐钦设的御宿镇,这义仓也是头一个设在县以下的,
这可是皇帝和宰相们都盯著的,岂能乱来。”
將差不多九石八斗的麦送入义仓中,成为御宿镇义仓储备的第一批粮食。
登记签名按手印,给予一张纳义仓粮的凭证。
这一幕,
看的一眾人都很意外,
乡绅豪强们意外,
升斗小民们更意外。
啥时候,这征粮时不想著法多收,还会把送去的粮给推出来的。
有人似乎突然回过神来,激动的大声问,“杜仓督,这一石粮只加二升雀鼠耗吗?”
雀鼠耗,名义上是补偿仓储损耗,可实际上这也是地方官吏们的一个灰色收入,
甚至到底加征多少,也往往是各地说了算的,
隋乱年间,这雀鼠耗甚至一石加二三斗,甚至有加四斗的。
而如今,居然统一了这个雀鼠耗,一石只加二升,还规定了这个耗羡加征,得入公帐,成为地方官府的公费。
將取代公廨钱放贷收息,用於公廨支出。
原来一石加二三斗,甚至四斗,现在一石只加二升,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。
过去课户,一丁一年要纳地租两石,可纳粮要送到州县,结果两石粟,要加五六升的斛面,还得加上五六斗的耗羡,实际负担增加了三成左右。
罗二也是清楚这些,所以今天都是提前多准备了的。
结果,居然不踢斛淋尖,还只每石加二升的耗羡。
还剩下了两石五斗的麦子。
罗二觉得这是因自己女婿是司徒,昨天皇帝还在他家喝过酒的缘故,坚持要把这剩下的两石斗麦子也送进仓。
“罗二哥哎,真不能坏了规章制度。你这两石半麦子,可以捐入社仓嘛,
咱这不是还有社仓嘛,完全民间村社自己所设,自愿捐献,自己管理,救助本社村民优先。”
在杜仓督的一番劝说下,
罗二最后决定,把这剩下的两石斗麦子也不拉回家,捐进御宿社仓,这是乡民们自己管理,不强制缴纳。
“想不到啊,
这义仓粮亩纳二升粟,还真就是二升,百亩地两石粟,再加四升鼠耗而已,一点斛面都不收。”
眾人都是议论纷纷,这样的好事,还真没遇到过。
除了社里的义仓,会里的会仓收粮,不管那些,官仓纳粮哪见过这样的。
习惯了以往的那套,现在还突然有点不適应呢。
各家的牛车拉著粮过来,陆续完粮,
几乎家家都是按老规矩多准备了粮,然后都没有多收。
有罗二带了头,其余乡绅们倒也没谁好意思,把剩下的那几石几斗的粮再拉回去,也都捐入社仓。
郭二郎也趁机对围观的乡民们道:“诸位父老乡亲,朝廷新政,惠及百姓。
这义仓粮亩纳二升,一石只加二升的鼠耗,没有踢斛淋尖收斛面,这马上也秋收了,大家赶在入冬前,儘快把这义仓粮缴纳了。
就咱本乡缴纳,也无须送到长安,方便著咧。
接下来,镇里要开始组织大索貌阅,严查诈老诈小,隱匿人口,没有户籍的要抓紧来登记为客户,
客户无须纳租调,有了户籍以后,也是朝廷编户良民,再不用提心弔胆过日子了。”
“这个冬季还要清量田地,镇里所有田地都要重新丈量,然后確权换契,大家相互转告,如实申报,配合丈量,完成登记確权换契,谁要是隱匿田地,到时可是要没收充公的。”
···
普济院中,
大皂角树下,
十男十女,二十名院中孤儿站成两排,
院长牛义感看著这群孩童,也有几分不舍。
“这是代王府送来的新衣,你们都去换上吧,一会呢,你们就去无极堡,跟著去长安。
你们是幸运儿,能被天子和宰相们选中领养,不管是进了宫还是去了宰相家,一定要自强自尊自立。”
李恩义站在那里,听著院长的谆谆教诲,目光却不由的瞥向旁边的李恩泽。
李恩泽是二班的班长,跟他同龄,也是十岁了。
他將前往代王府,由代王领养。
李恩义很羡慕他,他被皇帝选中,要带到宫中同功臣子弟一起抚养。可內心里,李恩义其实更希望能够是代王领养他。
在他心中,代王是他的父亲。
如果能跟李恩泽换一下,他会毫不犹豫。
另一边,几百双同学们的目光望向这二十个幸运儿,充满羡慕。
被皇帝、宰相领养啊,这是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
无极堡。
李逸终究还是要返京了,
不止他捨不得离开,一群孩子们更捨不得离开。
“淑娘呢?”
小丫头一人躲在角落抹眼泪。
“怎么了,捨不得这里了,我们有空就可以回来,离京城也就三十里地而已。”李逸抱起丫头安慰道。
“阿耶,淑娘想求你个事。”
“跟阿耶还说什么求,啥事?”
“我听说那家人日子过的苦,有常年臥病吃药的老娘,那家女人也身体不好,孩子又生的多,年年欠饥荒,还住在破窑洞里,我想,我想把我攒的钱给他们买五十亩地,再买头牛,然后请人给他们修一修几孔破窑,好不好?”
李逸知晓丫头说的是她隔壁村的亲生父母。
“没想到你攒了这么多钱啊?”李逸笑道。
“我问过了,买五十亩地再买头黄牛,再修一修几孔旧窑洞,我攒的钱应当够。”
“你为什么想这样做?”
李淑低头,“毕竟我是她们生的。”
“没想到你从小就这么善良,行,我让罗三帮你把这事办了。”
“谢谢阿耶,淑娘永远是阿耶的女儿,我长大了一定会好好孝顺阿耶的。”
“那你亲我一下。”
(本章完)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
- 导航
- 设置
- 字号
-
- +